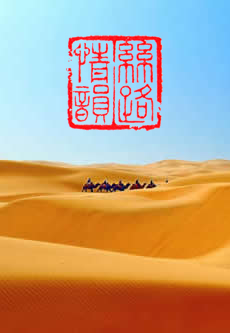洽川
黄河曲曲折折,时而平静时而激越,时而澄清时而浑浊地流淌了不知多少万年。三千多里的辛苦奔波,在到达内蒙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后开始急转直下,从这儿至河南郑州桃花峪的一千多公里中,河水落差竟达到八百九十多米,这是黄河全段落差最大的地域。而这最大的落差基本都在晋陕峡谷中。壶口的激昂跌落,龙门的湍急狭窄都是这段最代表性的体现,这一路河水像一个愤怒狂躁的猛兽在不停地跳跃奔腾咆哮着。
河水出了禹门口,流至合阳县洽川时,河面宽阔平静起来,在两岸的厚重黄土间衍生出温温的一处湿地来。数千个泉水喷涌相连,一百多平方公里芦苇摇曳丛生,鸥鹭翔集苍天,万鳞游泳碧波。这片温润的地方只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风光的旖旎秀美,也因为这里衍生留传了千古的脉脉情爱。周文王和有莘国公主太姒的爱情故事在此传说,《关雎》一诗正因此生,居于《诗经》首篇。瀵泉中的“东鲤瀵”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处女泉”,更是一处圣洁之水,泉水四季常温,芦苇生成天然的屏障。在以前,只有临出嫁的女子才能在这泉水里沐浴。美丽的女子从泉水中清新地走向新的地方,组成新的家庭,繁衍生息。
世间可以动人心者,惟因世间有情。而能历久弥新,咏唱不止的恐只是爱情。古今中外,天上人间,甚至地狱都有人吟唱着这深情的文字。《长恨歌》、《牡丹亭》、《红楼梦》等等多少文字,以及《聊斋志异》中的种种爱情故事,人神鬼兽,草木花鸟都为着这个情字笑哭奔走。一个“情”字真是让“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上天入地,流行人间。
逝者如斯的河水,苍苍如海的芦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温馨在这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惆怅也在这里。
世间惟有爱情才能让人活的有血有肉。帝王将相因此而平常,渔樵农牧因此而伟大!
上锣鼓
上锣鼓是东雷村村民世代沿袭下来的祭祀仪式。村子临黄河,滔滔河水从村旁流淌,仪式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产生。这里是夏商周时的有莘国之地,仪式的产生从现在的装扮看至少应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吧。
看吧,火把燃烧着举起来,火的龙在两队强壮男人们的如雷呐喊舞动中对角冲出。汉子们赤裸着上身,头上插着禽鸟的羽毛,戴着用葫芦、核桃皮做的眼睛和通天帽头饰,用草绳拉成的胡须,腰围着布条,蓑草,兽皮……这一切都是天地赐与的灵物,是和人生生共息的生命。披戴上它们,把锣鼓敲起,把身子舞起,把声音吼起,向这苍茫的上天,生我育我的厚土,向这滔滔东去的河水致敬祷告!
簸箕扇动而生的是风,锣鼓敲打而生的是雷,风雷是催生着万物的呀!风雷唤醒着天地水,养育着这世间万物。人民依着四季风雨的流转轮回,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
整体舒缓的“排锣”调,让同族聚集;小鼓引领,节奏稍快,舞者的动作开始多样的“流水”调,是向对方的挑战;铙钹高举,节奏急促,呐喊着争抢脚踏敲打对方锣鼓的“上鼓”调;锣鼓铙钹喧天齐响,背鼓追逐的“乱刮风”调……音乐越来越高亢激烈,舞者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忘我地舞吧!猛烈地敲打吧!争抢对方的锣鼓吧!争抢中的流血是真诚地祈求风调雨顺、祖先神灵庇护呀!身上头上布条帽子上的对虎、对鱼、牡丹莲花都是祈求子孙繁衍昌盛的象征呀!老者,你头上竖着的红葫芦还插着禽鸟的羽毛。葫芦是绵绵瓜瓞的繁衍象征,高高向上的羽毛也应是人间的通天符号吧?在锣鼓声中呐喊声中呼哨声中把这人间的生老病死,饥饱冷暖都告诉上天告诉祖先吧!保佑我们,保佑这黄河边黄土地上的人们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生生不息,世世安康吧!
踅面与混沌
(一)踅面
合阳虽临黄河,但缺水,因境内大部分都是黄土塬,处在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中间地带。缺水的黄土塬被称为旱塬,农作物都是靠天生长,人们都是靠天吃饭,日子便过的苦焦。
合阳气候和陕北高原接近,荞麦也成为了合阳人的主要食粮。踅面便是合阳人用荞麦做成的特色食品。面水比例合适后,用木杖顺着同一方向搅得稀稠匀当,便一勺子一勺子地倒在一张直径约2尺的大铁鏊中心,再用半月形的木踅子从鏊心向四周一圈一圈旋着刮开摊平,踅面之名便因木踅子而得。也有把“踅”作“旋”的,以为是搅和摊都是旋转的,我觉得这有些浮浅,因为还有其他的很多饼也是这样的做法。“踅”的来历似乎还可以探究。
面饼烙至八成熟,便铲出。后切成条,入锅即捞。大油去其涩,辣椒增其味,葱花添其色,用盐用味精拌之即成,干净利落。踅面可煮可炒,因人而异。合阳人嗜之如命,常拥挤摊店,个个吃的汗流满面,面色红赤。在外地工作的,听到踅面二字,便口舌生津,而起归乡心切。合阳再大的饭店,菜毕酒酣也必要上一碗踅面的。
只可惜外地人吃不惯,浅尝便辄止,望碗而兴叹,愧对了这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韩信发明的最早“方便面”。
(二)馄饨
在合阳,我吃到了一种圆形的有旋转纹的花馍,劲道而清香,当地的人叫它馄饨。民俗常说“西府乾县大锅盔,东府合阳喜馄饨。”正见合阳人对这种面食的喜爱,馄饨实际是源于中国本原哲学所说的“混沌”。
祖国的大地上,沿着河流大都有把不同造型不同功用的面花称为馄饨的。
《三五历纪》中说:“未有天地之时,混沌状如鸡子,溟涬始牙,蒙鸿滋萌,岁在摄提,元气肇始。”《淮南子》说:“有二神混沌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终,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老子》中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先秦哲学所谓的混沌,实际就是化生万物的阴阳本体。
在不同的地域,在婚丧嫁娶,添丁生育,传统节日时都会有不同的面花来表示不同的意思。如结婚时的双鱼花馍,祭祖用的“花大供”,春节捏的“燕盘”,大年初一吃的“锞”等,这些都是不同功用不同造型的馄饨。不管是怎样的造型和功用,其意阴阳相合通天,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生命轮回的符号意识不会改变。合阳的馄饨也是韩城、大荔、华县这一带馄饨的代表。
现在合阳人接待亲朋好友,在宴席上所吃的便是这种圆形的有旋转纹的花馍,这是馄饨中造型最为简单的一种。这种馄饨的纹路是从两边向内旋去,像一个两边向内卷曲的云纹,端午节有一种合包也是这种纹样。这种馄饨便是喜馄饨,实际就是祈求子孙繁衍昌盛世世安康的意思。
这种馄饨,可以馏热了吃,软乎清香。也可以烤着吃,焦黄干脆。合阳人吃这种馄饨,常常夹以油泼辣子和切成细丝的咸菜,更是别有一种味道。油泼辣子和咸菜的配合使人食欲大增,该吃一个的却往往吃成了两三个。摸着撑起来的肚皮,嘴里怪罪着这辣子和咸菜,心里却想着再吃几口呢。
印光法师(1861年—1940年),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合阳路井镇赤东村人。法师皈依佛门后字印光,自称“常惭愧僧”。
法师毕生弘扬佛法,修净土宗。因德行高泽被广而被后世尊为莲宗第十三祖,其影响所及佛门各宗,普天百姓。
叶圣陶先生的《两法师》中描写了见到的印光法师“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这是他的世相,和留存的照相很是符合。但我观仰法师的照相时,总觉得他凶巴巴的,眼睛真是射出光来,看穿了我这一颗鄙陋世俗的心,令人身生战栗而心生敬畏。
《两法师》中还描写了弘一法师向印光法师请益的过程。弘一法师只有两问,而印光法师却答至千言。这千言无非反复说些人伦天理,慈孝友恭,因果报应的话。
看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一则禅门故事:白香山学佛,参拜鸟窠法师。香山问法师说:如何才是佛法大意?法师答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香山说:此理三岁稚儿也知得。法师答:然八旬老翁亦难为!明代高僧莲池法师在《竹窗随笔》中也记录了类似的故事。所以俗世之人向法师问佛,总是希望得到些异于平常的教导和启示来,但却失望于回答的平常与浅近。岂不知人生在世间,有多少人能够按着这浅显共知的人伦天理,慈孝友恭去实行?而相信因果报应,收摄自己的欲望之心,以平常心平等看待世间万物,为善度人的又有几个呢?印光法师虽言说无奇,但世间有几个能按此修行呢?是真佛但说家常似乎就是这个道理啊!
一位朋友曾赠送过我一套《印光法师文钞》,我也和另一位朋友在长安卧龙寺求过一套。在法师所写的书、论、疏、序、跋、记、志中反反复复述说的也只是“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的道理。虽常以世间俗事为例说教,但却旁征博引佛教典论,可见法师对佛典研究之精深,通融。
在合阳也出过雷简夫、党晴梵等大儒大学问家,其在当地的教化作用自是很大,但印光法师的教化却广被天下,士农工商,男女老少,无不受其泽惠。大学问人常有,而净人妄心导人善行的教化者却不常有。在当今这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社会里,人们更需要在印光法师的文字里沐浴净心,以慈悲看人间,以行善为乐事。
中国的书法是很奇妙的一门艺术,也是世界上能成为艺术的惟一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它上使帝王下至庶民都对其沉醉迷恋,忘乎所以。
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再到隶书,文字的形象由纵式向横式发展,书写的自由度、符号化越来越强。隶书的产生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具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我们称隶书的产生为“隶变”。
隶书的萌芽在战国时期,两汉达到成熟和鼎盛。西汉的隶书简直古朴,基本没有隶书标志性的波挑,即所谓的“蚕头燕尾”。更加活泼生动,节奏明显,有着成熟符号化的隶书名品基本都在东汉。《曹全碑》便是其中之一。
巜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碑高二百五十三厘米,宽一百二十三厘米,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此碑无额,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郃阳莘里村,现存于西安碑林。
《曹全碑》的字迹保存较为完好,风神俱在。文字清晰,结构上横式舒展,有翩翩飞动之姿。书法工整精细,秀丽遒劲,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特征。此碑碑石精细,碑身完整,是目前汉代存世石碑中的精品。
作为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曹全碑》出土后,在后世学人的心目中地位极高。清孙承泽、康有为、徐树钧都赞赏此碑,以与《礼器》、《乙瑛》、《史晨》等碑同美。与其同时代拙朴厚重的《张迁》相比,《曹全碑》更像一位翩翩君子,不激不励,中正平和,风规自远。
当代人因为时风所致,在图式化追求上颇费心力。厚大拙朴以及夸张变形成为一种流行的审美趋势。《张迁》、《好大王》、《大开通》以及砖陶刻画等等成为取法热门,而《曹全》、《乙瑛》、《史晨》等等被闲搁冷置,因为其中正平和不激不励的风格在这猎奇炫巧的急功近利中太不容易引人注目了。《曹全》被列为秀美一路,很少为人取法。长安城中的合阳藉书画家马河声先生临过一册,形质兼备,颇见精神。
《曹全》秀美是其外表,骨子里却是强劲的,像一位修为极高的儒将。曹全家在敦煌,碑石的书法也更像了近年在敦煌及周近出土的简牍。《曹全碑》的风格也迥异于在秦地的其它或早或同时的刻石,这不能不让人对书丹人的来历产生遐想。
汉无弱碑,《曹全碑》自是如此。